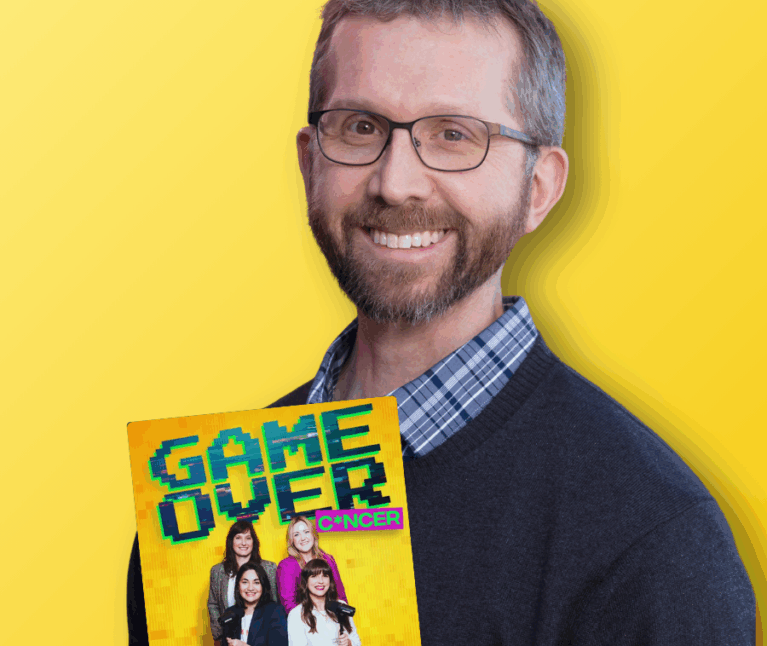毫不夸张地说,贾桑·齐默尔曼的诞生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身处癌症的儿童和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这位三次战胜癌症的老人——婴儿时期首次被诊断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在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之前,他的个人和职业生涯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包括近12年的科学家生涯!)。
如今,Jasan 是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健康基金会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s Health) 的基金会关系高级总监。他的科学背景、幸存者的视角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专业知识,助力他筹集资金,以解决儿童健康领域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最近,我们在 Cannonball 儿童癌症基金会 (CKc) 的朋友采访了 Jasan,讲述了他从治疗、生存到科学研究和服务的历程。
观看精彩的视频广播或阅读一些精彩内容,以了解我们团队中这位非凡的成员。
您曾三次战胜癌症。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抗癌历程吗?
我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是在1976年,当时我大概六七个月大。我的颈部左侧患有神经母细胞瘤。肿瘤被切除后,我接受了颈部左侧的放射治疗。那次放射治疗很可能导致了我15岁时的甲状腺癌。我做了甲状腺切除术和放射性碘治疗。后来,21岁时,甲状腺癌复发了——我接受了更大剂量的放射性碘治疗。我最后一次癌症治疗是在1997年,所以现在快30年了,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经历对你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又是什么帮助你挺过来的?
我15岁那年,抑郁症就发作了。我不想谈论它,我把它埋了起来。从15岁到30岁出头,我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很差。总感觉缺了点什么。除了感觉心情不好之外,我至今都无法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
我在湾区找到了一个青少年和青年癌症患者及幸存者互助小组。我真的很想去,但又不想去。我会去那里,停车,坐在车里听二三十分钟的广播。最后,我还是去了。我记得第一年,除了说“我是Jasan,这是我的癌症病史”之外,我几乎什么都没说。
但确实有几个人积极参与了倡导。我感谢他们激发了我的这个想法。
这些年来,您讲述故事的方式有何变化?
一开始是“这就是我的故事,我是个幸存者,耶”……我只想快点结束。后来变成了“这就是青少年和青年癌症幸存者的生存状态”。现在……我谈论的是患者应该如何成为研究中的平等伙伴。我已经在这方面奋斗了近50年——我想利用这一点。[癌症患者和幸存者]想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想被告知我们需要什么。
在进入融资领域之前,您在生物技术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转变?
和所有儿童癌症幸存者一样,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申请了几次医学院,但都没被录取。大学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妈妈说:“你应该去读研究生。” 我最终进入了罗马琳达大学学习微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圆满的开始,因为我(婴儿时期)在那里接受了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
我做了将近12年的科学家。这份工作很有趣,但也非常乏味。[最终]我被解雇了,这真是太可怕了,但我当时已经在旧金山大学开始攻读非营利管理硕士课程了。那次被解雇大约是在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得以转到帕洛阿尔托一家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基金会。起初,我考虑过癌症宣传,但当时我做了很多志愿工作。我突然顿悟:“我会一直与癌症抗争,这会让我精疲力竭。这对健康很不利。”
现在我领导着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健康基金会的基金会关系团队。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将我所关心的个人、职业和志愿工作融为一体。最棒的是,我不仅仅为癌症筹款,尽管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份工作让我保持平衡,不至于总是被癌症困扰。
患者讲述故事在研究领域扮演什么角色?
故事的力量无比强大——它驱动着人们。科学本身很复杂。但当有人说:“所有这些科学知识都帮助了我,现在我好了。” 这句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我们在斯坦福青少年和青年癌症项目的患者和家属咨询委员会上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现在是否是这位患者成为志愿者或参与倡导活动的合适时机?他们准备好分享了吗?有时,分享有助于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幸存者不应该感到压力,必须成为倡导者或讲述故事的人。
Cannonball Kids 的癌症对斯坦福的研究项目有何影响?
Monje 医生的 DIPG 临床试验——她有一位病人完全缓解,完全没有肿瘤。那是一个几十年来基本无法治愈且进展甚微的脑瘤。知道现在有孩子因为 CKc 的支持而活了下来——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每一笔捐款都意义非凡,无论是一美元还是 $100,000。
您希望更多人了解癌症康复后的生活的哪些方面?
治疗结束后,你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儿童癌症并非死刑,但绝对是终身监禁。这是一种家庭疾病,它影响着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患者。我还想说:“心理健康问题要处理好,别把它埋没。”
对幸存者有什么最后寄语吗?
如果你不想攀登珠穆朗玛峰,也不想成为筹款大户,那也没关系——去过上最好的生活,无论它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做任何对你最有利的事情。不要因为自己没有成为“超级幸存者”而感到难过。